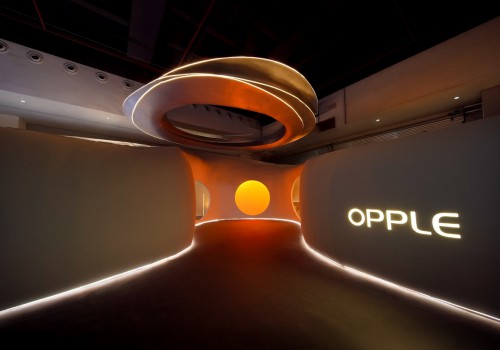喜桥从慕南山那里拿到借条并成功提前支取了2万块钱之后,便跟柳欢喜敲定了结婚的日期。这日期她不想再跟唐翠芝商量,她也不信什么天作之合,她实在对结婚仪式都不感兴趣。甚至对于结婚本身,她都说不上是不是真正的喜欢,她只是被一双无形的大手给一直推着,抵达那婚姻的山崖,如果不纵身一跃,跳进那山崖下的水潭,怕是会滚落进山底的碎石堆里,尸首全无。
柳欢喜高兴坏了,他抱着喜桥连转了三圈。这让喜桥觉得有一些愧疚,并且不理解柳欢喜为何会如此兴奋,他像一个得了糖果的孩子一样乐不可支,他的脸上,有成年人难以见到的单纯与快乐。似乎,他拥有了喜桥,就拥有了整个的世界。喜桥每次见了柳欢喜的样子,都带着一点微微的嫉妒和醋意,她真希望他能将那种爱情中的幸福,给自己分一点。她始终 和他隔着距离,她想就是因为他太过热情地陷在其中,而她,不过是在那团篝火外站着,就像隔着一条河,观望对面的火,那热量传递过来时,还是凉了大半。
结婚日期定在开春的那一天,在北方,虽然开春了也还是凉,可是至少能够穿婚纱在饭店门口迎宾了。柳欢喜说,一定帮喜桥定制一身最漂亮的婚纱,可是喜桥拒绝,她说租一套就是了,谁还会将婚纱拿出来穿第二次呢?如果耳环戒指银饰都可以出租,她也不怎么介意去租一套回来,她不知道这些东西,对于一个几乎不怎么佩戴首饰的人,究竟有何意义,难道是一百年以后给儿孙们增值?可是那时她都化成灰了,增值又与她何干?
喜桥第一次问及柳欢喜的存款数额,柳欢喜有些躲闪,但还是说了:你知道,喜桥,我不想跟父母要钱,他们身体不好,也需要用钱,或许,办完婚礼,我也所剩不多,房子首付再攒上一年的钱,也差不多了。在此之前,还得委屈你,跟咱妈好好解释一下,我们的婚礼,也怕是只能在……旧房子里,过了。
喜桥忍不住笑:感情之前你给我妈说的那些话,还都是吹牛啊?
柳欢喜红了脸:知道咱妈就好甜言蜜语,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冲上去,其实,我不太擅长这个的,嘴上说着,心里实在慌得很,真怕老天爷惩罚我。不过我保证肯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,就冲咱们两个年薪过十万,怎么着也不会在省城饿了肚子不是?
喜桥抱住他,将手环在柳欢喜的脖子上,而后在他的脸颊上,轻轻地印下一个温暖的吻。她不想吻他的唇,因为她忽然想起,自己早晨吃了辣酱,她不是怕辣着了他,而是觉得自己不干净,她想在做他的新娘以前,她需要好好地清洗一下自己,不管在结婚以后,她可能会变成一个怎样邋遢的、不爱整洁的、穿着随便的女人。
立春那天结婚的消息,唐翠芝知道后,有些不悦,喜桥知道她是觉得没有赶在年前结婚,可以多收一笔女婿过年时的上门费。唐翠芝对一切需要掏钱给别人的日子,都忘得一干二净,而对一切别人会孝敬她的日子,都记得一清二楚。如果逢上过年,喜桥去婆婆家,定可得到一笔新媳妇上门费,而女婿初次登门,也少不了给岳母大人献上一笔。喜桥有时听唐翠芝这样计较,恨不能将她脑子像更换电池一样给挖出来,换成一个大公无私型号的。
但喜桥是断然不会跟唐翠芝争执的,她只是听唐翠芝自己发了一通抱怨,并给予喜桥一番如何苛刻对待公婆的经验之谈后,打一个哈欠,说自己累了,要睡觉了,便算是敷衍了她。唐翠芝不罢休,在临睡前还要大嗓门地再问一句:金喜桥,你在不在听我说话?!这些你现在不记着,嫁过去之后,早晚会吃亏,我当年就是被你爸给骗了,早知道他们金家这么穷,我可不会嫁给他!
喜桥忽然想起来,试探着问道:那么,您老人家条件那么好,当初应该嫁给谁才对呢?夏风?
唐翠芝“呸”地一声,吐出一口唾液来:嫁给他那穷光蛋?!都是他害苦了我!我一辈子都栽在这个男人身上了!我恨他都来不及,怎么会嫁给他?!
喜桥的心开始绞缠在一起,有些疼痛,她知道真相就在这句话里,她的人生的钥匙,也在这句话里。她需要再靠近一些,确定这一把钥匙的型号,是不是跟过去的一扇门,能够完全地匹配。
喜桥靠近话筒一些,却将声音压低了道:那么,你本来是想嫁给赵思航的,却阴差阳错地因为什么不便道出的隐秘,而被夏风给耽误了,是么?
唐翠芝终于警觉起来,像一只老狼探到了敌情一样,立刻收了话题,警惕道:你问这些做什么?是不是有什么人联系你了?不管怎样,你都是我肚子里掉出来的人,别人怎么说我不管,但是你必须听信我说的一切。
喜桥叹气:好吧,那我睡了,晚安。
唐翠芝还想说些什么,但是喜桥早已挂了电话,并很快关了手机。
喜桥没有想到,距离结婚还有两个月的时候,唐翠芝就赶到省城,执意要跟喜桥住在一起,并美其名曰,帮她做婚礼顾问。喜桥心里恨,知道唐翠芝这是暗示她要大包大揽,将每一个细节都要干预控制。想到这些,她看着唐翠芝在房间里女主人一样来回走动,收拾东西,还自以为是地将东西的位置重新进行摆放,她的心里,就生出惧怕,好像有一群小鬼,在房间里来回跳动并时刻监控着她一样。
婚宴所在的酒店,因为没有提前半年甚至一年预定,喜桥打了很多的电话,才最终确定下了几个空闲之处,并打算与柳欢喜在周末集中过去看看现场情况,然后将之确定下来。唐翠芝自告奋勇,要一起去,况且她不想在家里当孤独的守门人。喜桥本来已经开了门,打算下楼梯的,可是听见唐翠芝甩出一句:你们两个就将我当空气吧,喜桥又退回来,帮唐翠芝拿了围巾,带着一点无奈道:走吧。
柳欢喜没有车,所以三个人只能打车前往酒店。就在路口等车的时候,唐翠芝就开始对柳欢喜发射第一颗挑剔的炮弹:连辆车也没有,以后你们两个怎么上班?天天挤公交,小心怀孕了连孩子给挤掉了!
喜桥头皮一阵发麻,她很抱歉地看一眼柳欢喜。还好柳欢喜宽慰地看着她笑了笑,而后安慰唐翠芝道:妈,我保证不过两三年,我们两个肯定有车有房。
喜桥吓了一跳,而唐翠芝早就神经敏感了:有房?
柳欢喜脸色变了样,知道自己说漏了嘴。喜桥赶着抢过去:妈,我们那房子,等着人家交工然后再抽出时间装修,可不得至少一年以后嘛。
唐翠芝上下审视了一遍一脸严肃、大气不敢出一口的柳欢喜,带着一点质疑,提高了嗓门道:真的么?什么时候,能带我去工地上看一眼?
喜桥又急急忙忙地接过去:妈,着急什么呢,还是先拣要紧的事做完再说。等我们忙着装修的时候,你想不看不当总策划还不行呢。
唐翠芝白了喜桥一眼:你今天怎么这么多嘴多舌的,还没结婚呢,嘴就长别人脸上去了!
柳欢喜又小心翼翼拍马:妈,我们马上不就是一家人了嘛,哎,车来了,快上吧。
匆忙之中,唐翠芝也顾不得责备,慈禧太后似的,在柳欢喜搀扶下,进了车,一屁股坐下,又整整衣服,而后给喜桥下了一个威严的命令:让司机带我们先去看最豪华的那家酒店。
最豪华的那家酒店,恰好是喜桥跟慕南山去过的蓝山酒店。喜桥从心底抵触这一家,但她却找不到合适的理由,阻挡唐翠芝和柳欢喜的高涨热情。尤其是柳欢喜,在选择酒店上,毫不吝啬,好像他自己突然有了一大笔花不完的钱似的。喜桥当然知道这是因为她弄到了2万块,帮他凑齐了5万块的彩礼,过了唐翠芝一道难关的原因。可是作为人生中的第一次也希望是最后一次的婚礼,喜桥却不希望带着不好的回忆,从此处进入婚姻的大门。
喜桥百般挑剔蓝山酒店的服务,从菜价挑剔到环境,从环境挑剔到服务,从服务挑剔到气味,就差指着服务员挑剔人家一脸麻子影响婚容了,服务员有些不悦,但没有甩不好听的话,只是扭过脸去,视喜桥为无物,不再理会她的任何问题。
唐翠芝在一旁气坏了,当众指责喜桥:别以为我不知道,你这是想省钱,羞不羞啊你,一个女人,要不是二婚,在结婚这件事上这么节俭,以后真过起日子来,有你吃苦头遭人克扣金钱的时候!
这几句真是一箭双雕,连带着将没有招惹唐翠芝的柳欢喜也给一起骂了。柳欢喜面带愧色,好像真的就已经在婚后亏待甚至虐待了喜桥一样。几个服务生面面相觑,继而又小声嘀咕着什么,最后,那个被喜桥给挑剔的服务生,假装被旁边的女孩子给挠了痒,咯咯笑了起来。这笑声跟一盆洗脚水一样,泼在了喜桥的脸上,身上,还有心里。她甚至担心那个服务生在议论她和慕南山的闲言碎语。喜桥站不住了,她想自己必须逃走,而且是立刻!
喜桥拔腿跑出蓝色酒店,让柳欢喜左右为难,他是谁都不敢得罪,去追喜桥落下了唐翠芝,那是欺君之罪,而守着唐翠芝丢下喜桥,那就是丢了自己老婆。他就眼睁睁看着喜桥跑出酒店,而自己只能一边走一边回头瞅着唐翠芝,嘴里没有忘了可怜兮兮地恳求:妈,咱们先去看看喜桥吧,外面车多人多,别走丢了。
唐翠芝嘴上恶毒得让人怀疑她是喜桥的后妈:让她出门一头撞死才好呢!从小就逃跑,逃到现在结婚也不让人安宁!她以为世界是由着她造的啊?!她以为这男人都是一心一意地跟她过的啊,她不知道男人都是狼心狗肺的家伙吗?!
柳欢喜实在听不下去,也不想再继续被服务生们当动物园里猴子一样好奇观望,他只能硬着头皮丢下唐翠芝一步步走出酒店。等出了门,回头,看见唐翠芝一步不落地在后面跟着,那一刻他才知道唐翠芝是不会吃眼前亏的,这个未来的岳母,她更擅长秋后算账的惩罚方式。想到这些,柳欢喜忽然有些发怵,究竟要不要去追自己的未婚妻喜桥——这个难缠的老女人的小女儿。
最终喜桥还是成功逃过了蓝山酒店,在一家中等档次的酒店里定了婚宴。选择好每桌的价格标准,并交完押金的时候,唐翠芝一脸不悦,一桌才888元,那么点菜,看着真寒碜人。喜桥挖苦她:寒碜的是人,不是你。
唐翠芝正坐在酒店休息椅上,听见立刻跳了起来:你说你老娘我不是人啊?!
喜桥也不着急,只慢腾腾又加了一个字:我是说,寒碜的是别人,不是你。
唐翠芝在那里站也不是,坐也不是,只好将旁边小桌上的纸巾忿忿地连抽了3张,狠狠地擤了擤鼻涕,又重重地投进旁边的垃圾筐里,这才一屁股坐下去,与喜桥背对着背怄气。柳欢喜又做了调解员,不过在奔波了这么几天还只是解决了一个定酒店的问题后,他明显有些疲惫,哄人的耐心也日渐弱了下去,当然,主要是针对唐翠芝。柳欢喜昔日的那种万丈豪情,在这个真实存在着的岳母面前,像被修剪过的大树,枝杈全无,只剩光秃秃的一根主干,在那荒原里空茫茫立着,连个同情的过路人都没有。
两个人别扭一阵,还是要在柳欢喜的好言相劝下,一件件继续下面的行程。在锁定出席名单的时候,除了各自的同事、朋友、同学之外,喜桥家和柳欢喜家的亲戚,再次成为争吵的焦点。喜桥觉得两家的亲人来就可以了,至于亲戚,邀请人家也不会千里迢迢地过来,也不至于为了他们而雇车过去,况且即便是来了,也没有地方住,需要另开宾馆,这同样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或许给的礼金连宾馆费都不够呢。
唐翠芝说不过来可以,但是要在两家再各办一次。否则,轻慢了各自亲戚,以后还怎么相处?喜桥觉得烦,随口而出:就这一次还不想办呢,还办三次?!我们又不是有钱没处花了,也不是离家千里迢迢,请几个亲戚做代表就可以了。
唐翠芝不答应,说在亲戚面前丢不起这个脸。而且照老家的规矩,女儿要先送出门,也就是在老家里办完喜酒,才能正式结婚。喜桥抢白她:那么你花钱送我好了,我反正不坐花轿,嫁我这个闺女,省钱得很!
一句话憋得唐翠芝直翻白眼,平息了半天,才吐出一句:你可不就是个省钱的货么,连买“三金”都挑最便宜的,人心隔肚皮,到时候嫁过去,有你吃苦头的!
喜桥冷笑:你以为这是封建社会,一嫁了人,就进了火坑么?况且我也没你命那么苦,找谁谁不娶。
唐翠芝腾地站起来,扯着嗓子冲喜桥也冲旁边的柳欢喜吼:忘恩负义,当初,我怎么没堕了你!如果不是你,我现在命没这么苦!
眼看着这火越扇越旺,柳欢喜赶紧将喜桥推到门外去,让两个“激动分子”都冷静一下。喜桥在楼道里还想嘟囔,柳欢喜叹气:姑奶奶,你们就都省省吧,还没有结婚呢,我夹在你们中间,都觉得累了。
喜桥看着柳欢喜无奈的视线,终于咬咬牙,半天吐出一句安慰的话:辛苦你了,欢喜。
柳欢喜给她一个并不有力的拥抱,又拍拍她的后背,没说话,而是进了门,并将门轻轻关上。喜桥听见唐翠芝鬼哭狼嚎似的的干叫,觉得浑身无力,倚着年久褪色的木质栏杆,坐在冰凉的台阶上,微微闭上了眼睛。
喜桥是在一天之后,才注意到江中鱼的未接来电。她其实是顺手将江中鱼给拉黑了的,所以他的来电显示,也便没有提醒,而是以一个符号的形式,在手机的上方标示出来。喜桥将那个来电黑名单里的时间等信息看了一会儿,决定不回复他电话,而是发一个问号过去。喜桥并没有关掉黑名单的功能,所以在江中鱼很快电话过来的时候,依然是提示他忙碌。江中鱼只好短信,只有一句话:想你。
喜桥淡淡一笑,第一次发现,她对江中鱼的留恋,已经在慕南山带她与江中鱼和美可擦肩而过的时候,淡得快要像风中的蛛丝一样,断掉了。她只回复过去一个笑脸的符号,她不想说一个字。
江中鱼当然是聪明的,他换了一个电话给喜桥打了过来。喜桥一时不知,接通了。听见江中鱼的声音,喜桥愣了一下,继而冷淡回他:有事么?
江中鱼很煽情地称呼喜桥为“老婆”:老婆,你真的忘了我了吗?
喜桥心里冰天雪地一样:忘又怎样?不忘又怎样?我要结婚了。
江中鱼半天吐出一个字:哦。
喜桥其实期待江中鱼能像个大男人一样,问他需不需要钱用。可是,江中鱼什么也没有说,好像那笔8万块钱,被他给忘记了,或者,根本喜桥就未曾给过他,再或它被花掉了,也就等于不存在了。
江中鱼还想说几句废话:什么时候结婚?
喜桥冷笑:问这个做什么,新郎又不是你,你也肯定不会来随礼。
江中鱼没话可说,喜桥不想说出“吃软饭”之类的致命话打击江中鱼,不等江中鱼回话,就匆忙道:我有事,挂了,愿你和你的旅馆,还有新欢,一切都好,以后,不要再打电话来了。
喜桥挂了电话,顺手将刚刚江中鱼打过来的号码,也加入了黑名单。
做完这一切之后,喜桥忽然觉得恶心,想要呕吐,她跑进办公室对面的卫生间,不等掀起马桶盖,哗啦一下就将早晨吃的东西,全给吐了出来。
原本没有什么的,办公室陆枚正好路过,好心又带着好奇问道:喜桥,怎么了?怀上了吗?
喜桥脸色一下子惨白,忘了陆枚的存在,觉得世界瞬间坍塌。
喜桥给李响打电话,让她马上过来,她有急事。李响声音慵懒,说自己刚刚打完一场仗,实在顾不上她的死活了。喜桥诧异,继而明白李响说的还是离婚官司。喜桥忍不住叹气:咱们两个,一个为结婚奔命,一个为离婚挣扎,怎么就没有人在婚姻里过幸福平静的生活呢?难道女人稍微有点心灵世界,就得被赶出婚姻大门或者费尽心机才能进去么?
喜桥还想絮叨一阵,却听到话筒里有轻微的鼾声,她又试着轻换了两声“李响”,都没有任何回音。喜桥惆怅地挂断了电话,将手机放入书包的时候,无意中碰到自己的小腹,那点诗意的惆怅即刻消失殆尽,她想这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,而且,要赶在结婚之前,干净利索地干掉。
只是喜桥忘了唐翠芝有鹰一样犀利的眼睛,她在走进单元门,还没有迈上楼梯的时候,就已经觉察到了唐翠芝凌厉的视线。她还担心柳欢喜,她不知道在这剩下的一个多月里,她该怎样逃过这一劫难。她已经不想将这个糟糕的消息,告诉江中鱼了,这个男人,在她的心里,只剩下回忆,还有一笔不知何时他会主动提出偿还的8万块钱。
那么喜桥现在就是孤军奋战了,与已经一个半月她才在忙碌中惊觉的腹中的孩子。这个孩子现在不是她的希望,而是一场灾难的导火索,每留一天在肚中,就可能会给喜桥带来一天的痛苦与折磨。这痛苦与折磨不是身体上的,喜桥想即便是双胞胎,她也不怕,只是,这孩子偏偏不是柳欢喜的,而是跟她恩断义绝的江中鱼的。她曾经希望江中鱼能够给自己带来人生的稳妥,可是几年后发现,一切都付之东流。江中鱼不想结婚,也无意于这种世俗的生活,他只喜欢恋爱,不停歇地恋爱,一个接着一个,而喜桥不过是他行经的站台上,最浓墨重彩的一笔。那么这个站台上偶然结出的瓜果,当然不能任其放肆生长,即便是在秋天里烂掉也不行,喜桥除了干掉它,别无它法。
吃晚饭的时候,柳欢喜也过来了。喜桥坐在沙发上抱着一个靠枕,不停地嗑着瓜子,盘子里铺了厚厚一层瓜子壳,脚底下也散乱着堆满了各种果皮和垃圾。唐翠芝从厨房里探头出来,看到紧紧盯着电视看广告的喜桥,生气训斥:一晚上了,你也好歹动上一动,帮我打打下手,你还真将你老娘当成全职保姆了啊?!可你也没付我钱不是?
喜桥完全听不到唐翠芝的喊叫,倒是柳欢喜听不下去了,碰碰喜桥,让她过去帮忙,喜桥迷茫地看他一眼,表示自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。柳欢喜看着喜桥的眼睛,低声道:喜桥,你怎么了,一晚上都失魂落魄的,好像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。
这一句将喜桥吓了一跳,而就在这时,唐翠芝将一盘炒好的韭菜鸡蛋,砰一下放到玻璃茶几上。喜桥一紧张,就觉得肚子疼痛起来,那种陌生又让她恐惧的呕吐感,又随之而来。喜桥啪一下扔了手里的瓜子,跑进了洗手间。
呕吐了也就短短的一分钟,可是这一分钟却如同一年一样漫长,当喜桥整理好脸上的表情,洗洗手,重新打开门的时候,她看到唐翠芝就站在洗手间的门口,用一种让她毛骨悚然的恨意,死死盯着她。
洗手间距离厨房和客厅,有一个拐角,喜桥知道此时柳欢喜看不到这样剑拔弩张的对峙,所以她迅速地扭转身,重新进了洗手间,并将毛巾放入盆里,打开水笼头,试图用哗哗的水声,将她和唐翠芝之间无声的“巨响”,给压下去。
唐翠芝当然紧跟了进去,并随手将门给关上了。厨房里有锅碗瓢盆的声音,喜桥知道柳欢喜在厨房里正忙得热火朝天,而她和唐翠芝之间的这场注定要少言少语的战争,也暂时不会抵达他的耳中。
喜桥等着唐翠芝说话,而唐翠芝则在她的身后,幽灵一样注视着镜子里低头装作洗毛巾的她。就在她开始拿肥皂的时候,唐翠芝将肥皂盒啪一声关上,而后几乎咬着她的耳朵,用极刑逼供的声音,恶狠狠道:谁的?!
两个人都知道这个时候,谁都不能争吵,一旦其中一个大喊出来,那么全盘皆输,之前一切定饭店、买结婚用品、定来宾的努力,都付之一炬,而且,有可能,将喜桥和唐翠芝的个人幸福,也一起给葬送了。
喜桥将毛巾从水里捞出来,用力地扭着,水由哗啦哗啦的声音,渐渐变得淅沥,最后只剩那么一滴两滴的水珠,用最轻又最刺耳的声音,落在水盆里,又砸在喜桥的心里。
喜桥在心里一遍遍对自己说,一定要坚守住,一定要等着柳欢喜走了,即便是唐翠芝将她杀了,她也要现在一脸的微笑,应对唐翠芝,也应对正憧憬着爱与家的柳欢喜。
如果唐翠芝现在有一把刀子,喜桥想她一定会一冲动,将自己给杀了,不过或许,在怀上自己的时候,唐翠芝就想杀掉自己,否则,为何她一直对喜桥这样苛刻又无情?
但是喜桥还是抬起头来,对着镜子里的唐翠芝,将唇角上扬,笑道:妈,别大惊小怪,是中午单位肚子吃坏了。
唐翠芝显然对这个谎言,根本不会相信,只是门外有人敲门,然后是柳欢喜的声音:妈,喜桥,吃饭了。
唐翠芝一边应着,一边狠狠看了喜桥一眼,然后打开门,走了出去。
一晚上唐翠芝都在憋着,但脸色已经难看起来。柳欢喜看着两个女人默不作声,有些不知道该说些什么,只好埋头苦吃,并用时不时地给两个女人夹菜,试图来一点一点敲碎那尴尬成冰的空气。不过那空气结冰的速度,远远超过柳欢喜敲击冰层的速度,所以很快,柳欢喜在唐翠芝砰地丢了盛汤的勺子之后,放弃了这样的努力。
柳欢喜本来打算饭后留下来刷碗拖地,多干点家务来缓和气氛的,不过唐翠芝摆明了要赶他走,在他拿起笤帚时,用不容置疑的语气,呵斥住了他:大男人,扫地多没出息,放着吧。柳欢喜觉得自己很像祥林嫂,讪讪一笑,搓搓手道:那么妈,喜桥,天也不早了,你们早点休息,我,先回去了。
唐翠芝一反常态,立刻跑去打开了房门,道:有空再来。
柳欢喜看着黑黢黢的楼梯,扭头给盯着电视屏幕的喜桥道一声再见,知道等来的也顶多是喜桥的一声可有可无的“哦”,所以也不等她回答,就低头两步迈出了门。
门关上的时候,唐翠芝又顺势将所有的窗帘给拉了个密不透风严。喜桥看着唐翠芝快捷的身手,知道她今晚要办一个私人法庭了。喜桥忽然想起小时候,邻居家的姐姐与一个中年男人谈恋爱,被父母知道了,将家里所有门窗关得严严实实,而且捱到后半夜,才开始一场充满了一生都挥之不去的羞耻与辱骂的家族审判。
喜桥憋得难受,决定先发制人:有什么大不了的事,还非得拉窗帘?我要没伤天害理、杀人放火!
唐翠芝将手里的笤帚啪一下扔出去几米远,并砸倒了一个角落里的易拉罐,那易拉罐咕噜咕噜滚了一会,觉得无聊,终于停下了。而唐翠芝的大炮,也在这时重重发出了一颗炮弹:到底怀的谁家的野种?!你最好老实交代,否则,我非得闹个鸡飞狗跳,让你这辈子都没有男人嫁!
喜桥冷笑:上梁不正下梁歪,骂人也不先看看自己。
唐翠芝在这句讽刺中,暴跳如雷,上来就将喜桥怀里的抱枕给扔到了电视机上,又扫荡了她面前的瓜子盘。喜桥捡起迸落在她身上的几粒瓜子,不紧不慢地磕开来,不打算再回应唐翠芝。
但唐翠芝已经开了火,闸门关不上了:你他妈的就是野种,我当初就该剁了你杀了你砍了你,如果没有你,老娘今天就不是这样悲惨的结局,你以为老娘愿意嫁给金家吗?!你以为我愿意要你吗?我他妈的费了多少心机,你都他妈的死皮赖脸地不从我肚子里滚出去,早知道你今天这样报复我,我他妈的就该狠心毒死你!
喜桥被唐翠芝这恶毒的话给吓住了,她嘴里的瓜子壳还半开着,她等了近三十年,终于亲耳从唐翠芝这里,听到了自己是邻居们议论的“野种”的真相。而更残酷的,是她的存在,在唐翠芝心里植下的仇恨,她不过是唐翠芝无意中结下的果子,跟赵思航或者夏丰,是谁不再重要,重要的是唐翠芝一心一意地想要干掉她,为自己的幸福,杀出一条血路来。她一直知道唐翠芝不喜欢自己,但从未想过,她是这样咬牙切齿地恨着自己,并将自己的存在,当成人生中一个竭力要谋杀掉的耻辱。
有几分钟的时间,两个人都陷入一种无法击破的情绪之中,谁都没有话,谁都在痛苦的边缘挣扎,期待有人来救,却最终发现一切努力都是徒劳。
喜桥觉得浑身发冷,有些打哆嗦,可是窗户依然紧紧闭着,并没有哪一扇被人砸开来。喜桥的牙齿甚至都在打颤,好像童年时害怕一个常常暴力打人的数学老师,总觉得这么多年,那个做错了题目时,候在旁边的耳光,还会啪一下扇过来。
鼓足了勇气,喜桥终于将那个困扰了她二十多年的问题,吐了出来:那么,我究竟是谁的孩子?
说完后喜桥忽然想起来,这是今晚这一场争吵,唐翠芝最初问她的问题。两个女人,在不同的时空中,生命却同时被一个同样的障碍,给阻挡住。而这一个障碍,又宿命般地,将她们连接在一起。
喜桥希望历经这么多年,唐翠芝在“谋杀”未成的现实面前,能够面对这一问题,让她知道自己真实的身世,及身体上的那个父亲。
可是唐翠芝却再次成为一头暴怒的狮子,她将身后桌子上的东西,全都哗啦一下子扫到地上去,而后用压抑的声音大吼:你他妈的没有权力问这个问题!我没有男人要,你也没有爹生养!是你毁了我这一辈子!
喜桥终于站起来,指着唐翠芝道:那好,既然这样,我跟你一样,留着这个孩子,像你折磨我一样,一辈子折磨它!
唐翠芝冲过来,重重地将一记响亮的耳光,打在喜桥的脸上,而后忿忿地吐出三个字:不要脸!
喜桥不知道什么时候,哭着睡了过去,醒来时刚刚天明,远远的有鸡叫声传来,客厅里狼藉一片,她有些恍惚,觉得像在梦里,或者在幻觉之中。她有些忘了昨晚发生的事,穿了睡衣起身,见唐翠芝大敞开着的卧室,和洗劫一空似的床铺,才再一次想起两人间曾经发生过的激烈的争吵与相互羞辱。
不知是因为吵架用力过猛,还是因为被这个忽然闯进身体里来的种子,给搅得失了重,喜桥走了几步,就有些头晕,她只能坐下,拿起手机,看到柳欢喜打来的三个未接来电,还有一条短信:喜桥,我吃了早饭,顺便路过你那里,给你送过去吧?
喜桥看看时间,是在半个小时以前,想想没有得到回复的柳欢喜,大约自动就认为喜桥不需要,所以回了自己家了。喜桥顾不上想他,倒是回忆起昨晚给唐翠芝负气所说的话,要留着这个肚子里的孩子,但事实上,话一说完,她就反悔,而且打算立刻做掉它,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只是,她要悄无声息地去做,不能让任何人知道,包括李响。
就在喜桥打算网上联系医院同时给慕南山请假一周的时候,忽然响起了敲门的声音。那声音带着一点犹豫,又带着一点胆怯,有些想逃离,还恋恋不舍。喜桥停下手里要拨打的医院电话号码,起身走向门口。她脑子里还想着肚子里的事,忘了看一眼猫眼,就随手开了门,门开后她漫不经心地抬头,吓了一跳,门外竟然站着气喘吁吁、满头大汗的夏风。
一时间两个人都有些局促和紧张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还是夏风先开了口:喜桥,我进省城,顺便路过这里,看看你。
喜桥这才觉得自己失礼,赶紧将夏风让进门来。但是进门后,夏风又坐立不安,很客气地让喜桥千万别沏茶倒水,他坐坐就走。喜桥看他欲言又止,知道有事要说,就直接道:夏叔叔,您这么远到省城来找我,肯定有事,我跟您就像父女一样,有事千万别客气。
不知道哪个词语触动了夏风,他竟然在喜桥说完这句后,流下一行泪来。那泪是浑浊的,很缓慢地从夏风满是皱纹的脸上流淌下来。那一刻,喜桥很想用自己的手,帮他拭去那滴饱满又苍老的眼泪,她甚至下意识地想要靠近他,就像一个孩子,靠近自己的父亲。尽管她与夏风来往不多,而且大多数都是童年时的记忆,但是即便那有限的记忆,也让喜桥在精神上,与夏风有着天然的契合感,好像一株庄稼,在泥土中最自然的伸展与融入。喜桥想起童年的时候,夏风曾经用胡子拉碴的脸,亲吻过她的脸颊,还曾经将许多崭新的小人书,收集好了,专门等着她去的时候送她。如果生命中没有父亲,她想她会在心理上,将夏风自动看作精神上的归宿,她想起他,就会有回家的踏实与幸福。
等着那滴眼泪流到地上,脸上的泪痕也快干了,夏风才窸窸窣窣地摸了好长时间的衣兜。那衣兜是在羽绒服里面的,大概左右上下各有一个,所以夏风摸到第三个,才舒了口气。喜桥看到写着鲜红囍字的红包后,就明白了夏风坐几个小时的车赶来省城的来意。
夏风将红包放到喜桥的手里,喜桥碰触到那双冰冷的手时,忍不住难过,她想起很多年前,夏风曾经拉着她的小手,穿过巷子,带她去家里吃饭,树上有明亮的阳光漏下来,洒在他们的脸上,暖洋洋的,喜桥喜欢眯眼看那叶隙中闪烁的阳光,好像那里有童话里的城堡或者梦想。而今夏风的大手已经枯树一样老去,那掌心里的温度,也凉下去了。而这样的改变,她却未能陪在他的身边,亲历或者见证。
喜桥想要推回去,夏风却握住了她的手,又用近乎哽咽的语气艰难吐出一句话:孩子,叔叔——只能给你这些了。
喜桥也只能收下。这个并不太厚的红包,在喜桥的手心里,却是沉甸甸的。喜桥不想问夏风是如何找到她所住的地方的,她知道这样只会让夏风觉得尴尬,但她也很清楚夏风来到这里并敲开她的房门前的种种挣扎与矛盾。不管他与唐翠芝曾经有过怎样的情爱纠葛,都已经不再重要,重要的是这个男人,在她的生命之中,有着如此不可替代的位置。这么多年过去,他还能记着那往昔的温暖,记着像女儿一样依恋着他的喜桥,并在从许多人口中辗转得知她的婚讯之后,亲自赶来,送红包给她,或者,只是借此看她一眼,这就足够她珍惜如此深沉的眷恋。
喜桥很想跟夏风聊聊那些过去的事,可是夏风的紧张无措和想要尽快离开的躲闪,又让她怕说得太多,惹他难过。她想不如去带他吃一顿饭吧,她愿意与这个温暖的男人,共进一份午餐,在靠窗的冬天的阳光里。